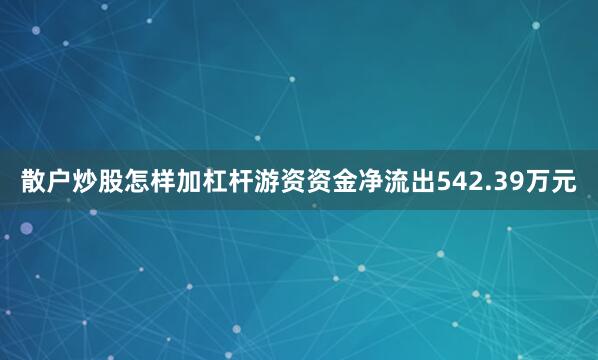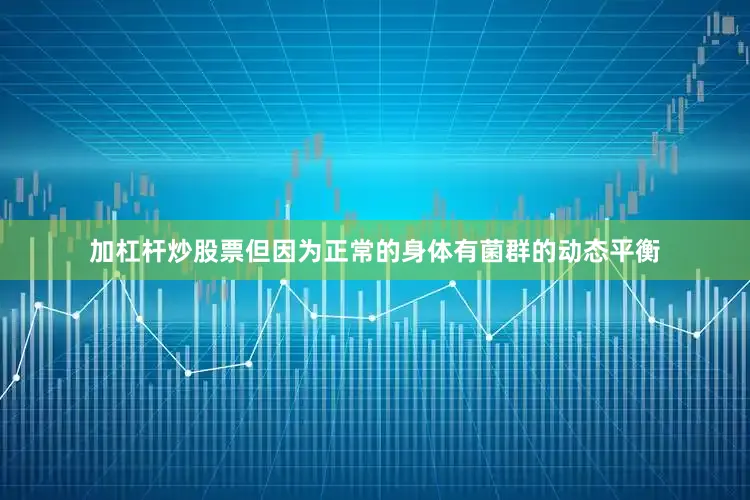2024年,乌鲁木齐出现了很多花园。这些花园的面积都很小,紧贴着人们生活的空间。在人们上学、通勤、吃饭的间隙,不经意地就会看到一簇簇的花朵和绿植,填满了城市的夹缝。这些一个个未命名的坐标,因为花园的出现,开始有了明亮的色彩,而这,仅仅是涟漪效应的起点。
建这些花园的,大部分都是留在新疆的年轻人。他们在小红书上找到对方,从网络空间跨越到具体的生活中,发展出了一个个社群。而城市,也在回应着他们。咖啡店、民宿、唱片店、小酒馆,宛如一阵阵的涟漪,逐渐碰在一起,在这土地上,扩散出一圈圈新故事、新风土。
文|詹忆梦、芬航
编辑|毛思雨
仍然有人
在城市里种花园
25岁,王冰莹不想再上班了。她产生了强烈的年龄焦虑。那种感觉很紧迫,时间好像在上班通勤之中被倍速地浪费掉。“不知道要去哪儿”,但是得找点事情做。她迅速地辞职。
展开剩余94%在游荡的七个月里,她去了乡村,短暂地实习,拜访各种机构,想着自己是不是要回家发展、是不是要做点什么。她在梦想愿景板里许愿,希望将来能在乌鲁木齐留下三个作品,而这个梦想很快就要实现——
在上海时,王冰莹从事的工作是景观设计。她为一些房地产项目服务,把空间做得很高级、很奢华。上海给人的感受也是如此,它没有问题,只是“太好了”。相比起来,乌鲁木齐的城市空间,就很不友好。“地铁只有一条,机动车却有8条,当我想过马路的时候,我都不知道对面是什么,要鼓起很大的勇气过这一条马路。”
王冰莹是在小红书上看到“万守新疆”的活动的——那是一个由本地青年自发组建的生活社群。当时,“万守新疆”的运营者鹤望回到新疆不久,想要让不断离疆又返疆的年轻人有一个可以说话、聚聚的地方。2023年1月1日,鹤望发起了一场读书会,并提前在小红书上做了预热。“没想到来了不少人。”那天,从聊书开始,聊到各自的生活,也聊出了一些共鸣。就这样,“万守新疆”正式成立。从一场读书会,发展出一系列轻盈、可持续的活动——聊天会、分享会、跨年聚会……这些线下活动,拉近了彼此的距离,也让“留下来”这件事有了更多支撑。
在“万守新疆”里,王冰莹那种对未来的沮丧一点点松动,浮现出一些新的念头。景观设计有没有可能结合“社区营造”,为这个城市做一点什么。这件事在王冰莹真正回到了新疆定居后有了进展。她邀请了苍苍加入,和“万守新疆”的伙伴一起组成了一个社区工作小组“乌龟营造”,专注于公共空间改造与社区花园建设。她想试试看,这些人与人之间激起的涟漪,有没有可能延展进城市的空间中,推动这些联结落地、生长。
图源:万守新疆线下读诗会
彼时,正是刘悦来挂职乌鲁木齐市城乡规划管理局之际。他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副教授,也是援疆专家,恰好在推动一个关于青年参与城市微更新与社区营造的项目。
在刘悦来的指导下,王冰莹和伙伴们进入到了城市最小的生活尺度——街道。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,能见度非常低。社区书记找了一辆车带着他们在社区转。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街道,旧居民楼旁,是一个没人打理被荒废掉的花园。
“冰封玫瑰”的构想开始成形。王冰莹想起,有一回,刘悦来带着他们去看学子路的绿化带。在这个狭长的地带,植物以一种极其规则的方式呈圈状生长。这并非是刻意安排,而是由于乌鲁木齐干燥的气候,只有被灌溉的植物才能得以存活。
夜色下的冰封玫瑰
图源:無予WooU包容性共益社区
那几天,王冰莹在网上刷到了一张冰冻花朵的照片,她想到,干燥的气候令植物枯萎,而严酷的寒冰却能冻住花朵。如果在街道上,用冰墙冻住玫瑰,说不定就能营造出不凋谢的玫瑰花园。
当玫瑰进入一座城市的日常生活时,有一些变化就这么发生了。春节的某一天,乌鲁木齐的市民忽然发现了这些冰墙中怒放的红玫瑰,宛如这座城市为市民献上的春节礼物。人们驻足、围观、低声讨论,爱拍照的女孩在这里留下了“人生照片”,也有人趁着夜色前去,等候深夜无人的时候,与满墙的冰雪、花朵独处。
市民们与冰封玫瑰合影
图源:王冰莹
她开始发现,浪漫是不需要语言的,它自然而然就能带着人们走在一起。而以往那些完美到苛刻的空间设计,除了把民众挡在了外面,也否定了那个在缓慢原生、未经规训的城市里的自己。
在小地方,
一千朵玫瑰找到彼此
在王冰莹和苍苍看来,在真正的实践中,这些花园,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属,而是由个体自发汇集在一起,就像波浪一样,慢慢生长出来。而这也恰似是哲学家所讨论的风土与文化的关系。日本学者和辻哲郎曾经提出“风土论”。他说,“风土是对某一地方的气质、气象、地质、地形、景观等总称”,同时,他强调,风土就是地球上的这一处有且唯一有的东西,而我们共同的文化,就扎根在其中。
玫瑰之前是乌鲁木齐市民自发投票选出来的市花。这跟乌鲁木齐的风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新疆处于冰雪黄金纬度带,雪季长达150多天。漫长的冬天,带来单一的灰白景观,也让人感到沉闷压抑。与之相对的,是乌鲁木齐街头一个个被称作“花池子”的小花园。这座城市有种花、经营家庭花园的传统,乃至成为本能。在维语中,人们把月季、蔷薇、玫瑰这一类花朵统一叫做“克孜勒古勒”,意为红色的花。
乌鲁木齐小区里常见的花池子
图源:苍苍
像“冰封玫瑰”这样的灵感,并不是城市里的偶发事件。在王冰莹构想“冰封玫瑰”之前,也有两个女孩,在城市里发起#种植一千朵玫瑰艺术计划。她们尝试用几毛钱的纸,加一根吸管,叠出一朵朵彩色的玫瑰。玫瑰越来越多,她们将这些玫瑰插在雪地里。乌鲁木齐的雪地,洁白干净,如同一块天然的展示板,将这些纸玫瑰衬托得明亮活泼。后来她们将这些纸玫瑰插在雪地里,也放在城市驿站中,让玫瑰自行漂流。
图源:王冰莹
不少人驻足观望,打量眼前发生的变化。她们也把玫瑰送给环卫工人和外卖小哥,有些玫瑰就放在驿站,自行漂流。现场有简单的物料工具,也有循环播放的教学视频。阿姨们自发加入了叠玫瑰的阵营。不需要语言沟通,仅凭着“共同参与”的共识,就能把玫瑰“种”满城市的角落。
类似的蝴蝶效应还在发生。在万守新疆和乌龟营造发起的“轮胎花园”中,他们发动市民一起动手。把废弃轮胎进行艺术改造,用来营造花园。一位维吾尔族外卖小哥看了许久,那是他出来跑单的第一天。当他上手时,他迅速用一些鲜艳的色彩画出了一些图像。在这些年轻人看来,那些不照着手机,随手就能画上几笔的路人,所拥有的自然、随性的想象力,恰恰是这个社会习惯于找模版、找答案的年轻人丢失的东西。
外卖小哥画下的随性图案
图源:王冰莹
每个花园
都会找到最好的朋友
现在如果有人问,你们在做的是什么事情?王冰莹会回答,我们在城市的缝隙里种花,以及带动别人种花。
回溯起来,很难说,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。
就像第一次做花园期间,他们也没什么经验,一位署名淼淼的志愿者留下一句话,“浪漫的花可以在任何地方盛开”,虽然不知道淼淼是具体哪一个人,这句话却成他们后续一系列行动的slogan。
图源:乌龟营造
就像鹤望刚回新疆时,自己也不能确定,这个事能不能成。他只是单纯觉得离疆又返疆的年轻人,需要凑在一起,为城市的发展真正做一点事情,于是发起“万守食堂”,请陌生人吃饭,组局“聊天会”,共同讨论留在新疆的理由。直到一位网友进了他的小红书群,沟通中,鹤望发现,这位网友是荒野新疆的创始人,也是一位返疆青年,做当地的自然生态和野生动物宣传和文创。这样的接触给了鹤望一种被点燃的感受——原来已经有人在他之前,做了一些他想做的事情。
唯一可以确认的是,这些看似清晰的行动,主要生发于人与人之间的微妙生态。“先找到想要靠近的人,漫无边际地聊完之后,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合作。”鹤望举了一个例子,“万守”生日会活动时他,和酒吧老板漫谈。酒吧老板提到,有堵墙很碍事,想找工人打掉。鹤望说,不如我们一起来打吧。于是,活动那天,成员们一起在墙上写下想要告别的东西,最后一起拿了锤子把它砸掉,活动效果让人难忘。
后来,很多人问鹤望,是从哪找到的这样恰到好处的一堵墙。“可能刚好有一个墙,有一个酒吧,有一个活动,这是自然发生的一个事情。”在一个场域里,人和人在一起,就会互相点燃、激发。
“万守新疆”2周年生日会上的砸墙仪式
图源:万守新疆
有意思的是,这些人并不是鹤望主动寻找来的。他只是发了一些活动信息和生活片段,就像是放下了一把种子,感兴趣的人便自然聚了过来。在小红书上,这样的连接更像是一种有迹可循的的吸引力法则:不是流量推送,而是基于“谁想看见我”、“谁能理解我”这样更私人的连接方式——先是审美、兴趣上的吸引,接着是一种生活追求的共鸣,最终带着人们穿过屏幕抵达现实,转化为共建。
鹤望自己也没有想到,短短一年间,他已经从小红书上“下载”了三四千人,包括王冰莹、苍苍在内——这几乎是一个人社交网络人数的极限。如今,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“伙伴网络”,摇摆舞社群、酒吧、咖啡馆……有的已经开始合作,有的还在等待机会。而城市,就在这样细微紧密的连接中,一寸寸重新织起。
“乌龟营造”“万守新疆”所搭建的花园地图与伙伴网络
图源:王冰莹
牵手之前,
我们先练习靠近
年初,“冰封玫瑰”盛开期间,鹤望和“摇摆新疆”商量着,在这个人流量密集的地方,发起一场摇摆舞快闪。考虑到天气寒冷,零下二十多度,本来想着跳个十五分钟就结束活动。结果大家一直说,“再来一首”,“再来一首”。就这样,音乐一直播,舞者一直跳,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。
在单一流量机制的驱动下,许多城市的公共形象被简化为高度符号化的标签,导致外部对乌鲁木齐的印象,也长期停留在“机场很大”“能歌善舞”“水果好吃”这样的层面。注意力即是经济,为了快速建立认知,城市的具体生活让位于固定的传播模板。
而在乌鲁木齐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们渴望脱离这种符号化想象,凭借自身经验与在地感受,开垦出一条重塑公共空间的小径。
“万守新疆”和“摇摆新疆”一起合作的摇摆舞活动现场
图源:鹤望
今年六月,王冰莹在乌鲁木齐的一场摇摆舞会上见到了许多熟悉面孔,而这场舞会的发起人,是本地推广摇摆舞多年的老塔,也是一位来自新疆省歌舞团的舞者。新疆的摇摆舞氛围从前几年一点点扩散开来。几乎在同一年,新疆出现了两个摇摆舞社群,“摇摆新疆”和“摇摆天山”。前一个社群是由四位女生发起,后一个社群的主理人是朱朱。
摇摆舞社群的出现,有点像是“种花”之外的另一种形式——更集中、更即兴,也更容易打开这座城市的被忽略的情绪通道。
新疆的“麦西来甫”是一种维吾尔族传统的聚会舞蹈,它并不指向某种具体的舞种,而更像是一种“跳起来”的氛围——没有固定的动作套路,却拥有鲜明的切分节奏,让人不自觉地迈出小碎步、沉浸其中。
快闪小舞台
图源:小红书「烟火生活季」
在一场场周末的舞会中,这群跳摇摆舞的年轻人逐渐发现,很潮流的舞蹈,与家乡的“麦西来甫”之间,竟有某种奇妙的契合:即兴的、松弛的、以节奏唤起情绪的集体律动,变得很自然。“摇摆天山”的主理人朱朱在持续学习摇摆舞的过程中,笑称自己变得“疆化”了。在小红书上,她将自己称作“摇摆古丽”。“古丽”,在维语中有美人、像花一样的女孩的意思。在乌鲁木齐上了七年学,她没有再去其他城市,而是干脆留在乌鲁木齐,既生活,也跳舞。
朱朱说自己是E人,喜欢人群中吸收能量。她发现,摇摆舞(Swing Dance)就是这样的一种具有人群聚集效应的舞蹈。
新疆有十三个世居少数民族。朱朱发现,很多维吾尔族人,自己就有很好的乐感和律动,“他们会很真诚、很自然地直视你的眼睛”,跟舞伴有很好的交流,自带舞台感。蒙古族人也有同样的优点,能够随着音乐摇肩摆胯。
快闪小舞台
图源:小红书「烟火生活季」
摇摆舞的魅力在于自由与松弛,没有固定的动作,也不要华丽的舞台,只要音乐响起来时,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晃动,产生微醺般的快乐。朱朱发现,原来在当代,快乐和放松也是很难的。“很多人的手没有办法高高地、自然地举起来,总是那样缩着。但是,如果你都不能把手举起来,那还有谁能帮你呢?”
在教学的时候,朱朱会观察人与人的互动。在跳舞时,人们需要先练习牵手,学会直视对方的眼睛,这样才能知道下一个节拍要往哪里去。人与人之间交流、连接的可能性由此产生,“我会开始欣赏你,发现你今天的耳环好好看。”它把人从虚拟的世界里拉了出来——只有在具体的关系场景中,人才会产生想念、共情、爱。
而摇摆舞恰好是低门槛的连接纽带,“不分民族、不问背景、不要报备。”“平时谁跟谁拉手啊,你跟好朋友都不一定拉手,跳舞的时候,拉手就形成习惯了。有的人一星期不见,就会很想他”,朱朱说。有一回,朱朱和伙伴们春游,本来只打算在民宿里聊天,有人带了威士忌,气氛一下热络起来,有人提议:“不如去山上跳一跳?”他们就真的动身了。那天正下着雨,但没人在意。“抑制不住想跳舞的心,不管,下雨也要跳。”
今年六月,老塔找到了朱朱,还有“摇摆新疆”的创始人,提出想在小红书在乌鲁木齐举办的“烟火生活季”活动中,做一场摇摆舞的快闪。所有人都穿上漂亮的衣服,聚在一块。这是老塔一直以来想要完成的事,“让喜欢摇摆舞的人在家乡畅快地跳舞”。
其实,在本地人眼中,乌鲁木齐从不缺少多元而新鲜的生活图景,只是它们沉在城市的缝隙里,一直缺少被看见和被认领的契机。挖掘与呈现这份深藏于街巷的、鲜活的城市烟火,让更多人看见、认领并爱上它,是小红书「烟火生活季」的初心。而这群年轻人所做的,则是与平台一起,将这些原本就存在的风土一点点挖掘出来,让它们重新浮出地表,成为城市日常中可感可亲的生活印记。
快闪小舞台
图源:小红书「烟火生活季」
朱朱原先觉得,乌鲁木齐一直离潮流很远,接受什么新事物都要慢一些,这次快闪活动后发现,这是一个很接纳、很包容的城市,人们永远兴致勃勃,等待着新鲜事物发生,一旦有人开了头,音乐就不会停,舞步也不会停。
在摇摆舞曾经盛行的年代里,人们不分你我地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BGM,在乌鲁木齐的舞会也是一样,“热情太高了,它会冲破界限,我们跳在了一起。”这是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、城市青年和外来者,在身体节奏中共振的乌鲁木齐。
编织生活的新地图
在这些留在新疆生活的年轻人看来,乌鲁木齐是距离潮流很远的城市,而在现代性的浪潮下,当地的小商店关了门,品牌连锁开张,时髦事物移植到了当地中,旧的凋敝了,新的闯入,新与旧之间似乎有许许多多的空白,显得有些割裂。
表层之下,这片土地的风土,如同潜流一般,缓慢地流动着。
陆晋生是一位地毯史研究者,十四年前,曾追逐着新疆地毯来到乌鲁木齐。在新疆的街头,人们习惯铺上地毯席地而坐,而在房间的墙上、脚踩的土地上,地毯在另一个更广阔的时空维度里,映射着这片土地的风土的起伏。
图源:陆晋生,1990年在乌鲁木齐的日子
在家庭作坊中,他看到人们用村里的桃树枝打磨成工具,在石头灶上放着一口小锅,煮着正在染色的毛线。他们从祖先手里得到了用葡萄皮、树叶和植物汁液等天然材料染色的工艺。在地毯上,人们留下,在编织时,他们爪印、割草工具、发梳——这些都是生活中得来的灵感。
在陆晋生看来,在这里,新与旧从不是替代,而是一种交织。从古至今,部落间的往来,把技艺留在土地上,而生活其中的人,又一代代将技艺拾起,继续编织下去。陆晋生说,他在那些地毯中,看到了“某种类似文明般崇高的东西”。
只要生活在流动,编织就不会停止。编织就像是祖先的赠礼,守护着日常秩序;编织也是一种修补,人们在不确定的生活中,用这种灵活的方式,织着生活的神性。这种柔韧性与创造力,足以应对加速变化的世界,延续着人与土地之间的亲近感。
图源:陆晋生
这一古老的逻辑,并没有在数字时代终止。城市里的年轻人以自己的方式延续着“编织”传统。有人在一端起头,就有人在另一端收束,有人收集植物汁液为城市染色,就有人用舞蹈为城市带来律动,在针线起伏之间,柔软而鲜活的地毯被编织出来,这依然是属于新疆的城市之毯,也是建立在本地经纬上的“新在地化叙事”。
生长于这一洞察的小红书“烟火生活季”,则如同一根引线,牵起那些散落在城市缝隙中的在地回响与行动轨迹,与年轻人的情感记忆一结一结地打在一起,绘制出一块块可被看见、可被共鸣的生活纹理——在这张毯面上,人与地方重新相认,日常重新生长。
从外地回到乌鲁木齐刚满三个月,苍苍有时候觉得失落,这座自小长大的城市对他来说变得既陌生又熟悉。但转念一想,也未曾是一件坏事,“因为我还是可以继续跟这些东西产生关联。我在新的城市累积的经验,过去已有的那些记忆,加上我现在的一些实践,都可以和它产生新的连接。”
最近,苍苍学会了观察植物。新疆的冬天长,这里春天来得晚,植物长得很慢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这些植物都在渡过它的休眠期,看起来毫无生气。而到了四五月份,植物会忽然之间接着一场雨、一阵风,迅速地长出叶子、花瓣、果实,变得热烈。
苍苍家的窗外有一颗梨树。一场雨过后,他发现它长出了两瓣叶;又一场雨过后,他发现它开出了花。他过往不曾感知到的,慢慢开花、结果。
对于时间的感知,万物都有不同的尺度。土地有“土时间”,花朵有“花时间”,涟漪的触发与扩散,也有相应的时间。 在那个不知何时到来的勃发瞬间,在新与旧的缝里,不知是谁,已经种下了一些花,等着时间慢慢开。
雪地里的一千朵玫瑰花
图源:無予WooU包容性共益社区
运营编辑:叶晨灏
三联人文城市是三联生活传媒旗下的城市整合传播品牌。以一年一度的三联人文城市奖、人文城市季、人文风土季为主线,创立了“小城之春”“你好陌生人”“光谱计划”等IP。在中国城市从空间转向人文的节点上,通过展览、论坛、演出、工作坊、报道、出版等线上线下多种形式,关注城市生活,激发公众参与,重塑城市人文价值。
三联人文城市联络方式:
发布于:北京市九龙证券,靠谱的股票配资平台,线上开户的证券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